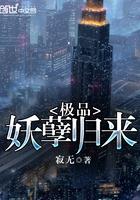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读历史故事学待人处世 > 第二章 水流不腐人活不输(第2页)
第二章 水流不腐人活不输(第2页)
南齐的徐文远也是这样一个人。
徐文远是名门之后,他幼年跟随父亲被抓到了长安,那时候生活十分困难,难以自给。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后来官居隋朝的国子博士,越王杨侗还请他担任祭酒一职。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了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维持生计,凑巧碰上李密,于是被李密请进了自己
的军队。李密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请徐文远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为自己效力。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李密答谢说;”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但却对王世充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像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我查看时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徐文远之所以能在五代隋唐之际的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之法,懂得灵活处世。
孔子门下弟子众多,他教育这些弟子从来不用一刀切的办法。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对吗?”孔子说:“对。”过了两天,冉有又问孔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对吗?”孔子说:“考虑两遍就行了,不用三思。"别人听了孔子对弟子的两种解释,就问:“您怎么对弟子的教育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为人鲁莽,所以我让他做事三思,冉有平时做事本来就优柔寡断,所以我鼓励他果断一点。”
点评
为人处世要灵活一些,行就做,不行就放,不要一根筋。
有些事不一定要亲自去办
为人处世与做人办事是不可分割的,但只有灵活的人办事不循常规,不依模式,他们就像“水"一样,遇到什么样的“容器",就用什么样的办法渗入。
孟尝君是齐国的名门贵族,几度岀任相职,是政界的实力派。但有一次他与齐闵王意见不和,一气之下辞去相职回到了私人领地叫薛的地方。
这时与薛接邻的南方大国——楚国正待举兵攻薛。与楚相比,薛不过是弹丸之地,兵力粮草等均不能相比,楚兵一旦到来,薛地后果不堪设想。
燃眉之急,唯有求救于齐。但孟尝君刚刚与闵王闹了意见,没有面子去求,去了也怕闵王不答应。为此他伤透了脑筋,几乎一筹莫展。
绝路之中老天给他降下了一线希望,齐国大夫淳于髡来薛地拜访。他是奉闵王之命去楚国交涉国事,归途顺便来看望孟尝君这位名门望族的。孟尝君抚额称庆,可谓天助我也。他早已想好了主意,亲自到城外迎接,并以盛宴款待。
淳于髡不仅个人资质好,善随机应变,常为诸侯效力,与王室也有密切的关系。威、宣、闵三代齐王都很器重他。闵王时代成了王室的政治顾问,且与孟尝君本人也有私交。
孟尝君决心已下,开口直言相求:“我将遭楚国攻击,厄在旦夕,请君助我。”
淳于髡也很干脆:“承蒙不弃,从命就是。”
后人猜测,淳于髡此行,可能是有目的而来,专为朋友解危的,只不过想让孟尝君亲自求他就是了。朋友之交,有许多心照不宣的东西,古来如此。
却说淳于髡赶回齐国进宫晋见闵王。正面的话题当然是要相告出国履行公务的结果,他真正要办的事情也早已盘算在心。
闵王问道:“楚国的情况如何?”
闵王的话题正投淳于髡的所好,顺着这个话题,淳于髡要开始展开攻心术,履行对朋友的承诺了。
“事情很糟。楚国太顽固,自恃强大,满脑子想以强凌弱;而薛呢,也不自量……"
话题意识性地流动,谈到薛,但不露痕迹。
闵王一听,马上就问:“薛又怎么样?"
淳于髡眼见闵王入了圈套,便抓住机会说:“薛对自己的力量,缺乏分析,没有远虑,建筑了一座祭拜祖先的祠庙,规模宏大,却不问自己是否有保卫它的能力。目前楚王出兵攻击这一祠庙,咳,真不知后果怎样!所以我说薛不自量,楚也太顽固。”
齐王表情大变:“喔,原来薛有那么大的祠庙?"随即下令派兵救薛。
点评
守护先祖之祠庙,是国君最大义务之一。为了保护祖先祠庙就必须出兵救薛,薛的危机就是齐的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闵王就完全不再计较与孟尝君的个人恩怨了。整个过程,淳于髡没有提到一句请闵王发兵救孟尝君,而是抓住闵王最关心的问题t也就是最大的弱点,旁敲侧击,点到痛处,令闵王自己主动发兵救薛,实际上是救了孟尝君。淳于髡的纵横术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
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不把事情做到极点,于情不偏激,于理不过头,这样才能保全自己。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长孙氏被册封为皇后。当了皇后,地位变了,她的考虑更多了。她深知作为“国母”,其行为举止对皇上的影响相当大。因此,她处处注意约束自己,处处做嫔妃们的典范,从不把事情做过头。她不尚奢侈,吃穿用度,除了宫中按例发放的,不再有什么要求。她的儿子承乾被立为太子,有好几次,太子的乳母向她反映,东宫供应的东西太少,不够用,希望能增加一些。她从不把资财任情挥霍,从不搞特殊化,对东宫的要求坚决没有答应。她说:“作太子最发愁的是徳不立,名不扬,哪能光想着宫中缺什么东西呢?”她不干预朝中政事,尤其害怕她的亲戚以她的名义结成团伙,威胁李唐王朝的安全。李世民很敬重她,朝中赏罚大臣的事常跟她商量,但她从不表态,从不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皇上要委她哥哥以重任,她坚决不同意。李世民不听,让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做了左武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皇后派人做哥哥的工作,让他上书辞职。李世民不得已,便答应授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皇后这才放了心。此后的朝政官任中,长孙无忌也经常受到皇后的教导,成为一代忠良。
长孙皇后得意时不把各种好处占全,不把所有功名占满,实在是很好地坚持了为自己留余地的原则。这样,不但不会使自己招至损害,而
且还使自己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进退有据,上下自如。
树大招风,在大功重赏面前,或身居简位之后,更要懂得知进退,留余地,更要善于“藏巧”,切莫锋芒太露,妄自尊大,以免功高震主,引火烧身。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不知进退的人的下场,他就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的年羹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