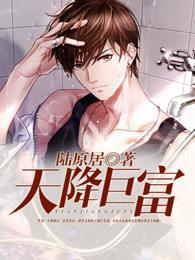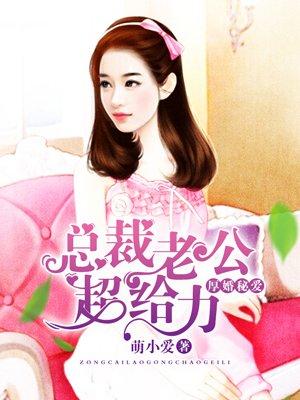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大明登基以后 > 第269章 只识太子(第1页)
第269章 只识太子(第1页)
文臣们毫不客气地向朱瞻墉直言进谏,皆视新政为荒谬之极,视之为乱政。
朱瞻墉嘲讽道:“乱政乎?呵呵,朕倒未曾看出何处乱了,若论不中听之言,尔等视之为乱政的政令,朕早于数年前已在金陵推行。若言乱,诸位可告知朕,金陵是否已乱?呵呵,反倒是金陵,已成为大明最为繁盛之地。”
“如今,百姓们削尖了脑袋欲入金陵,尔等可知否?想必不知,金陵人口已逾五百万,且仍在增长。”
“大明百姓总数不足六千万,金陵便占十分之一。”
“金陵之中,无论男女,即便是稚龄孩童,皆能识文断字,金陵有五百万读书之人。”
“在金陵,读书乃是百姓之基础,而非尔等士人之高高在上。”
“尔等告知朕,金陵何处显乱?”
“尔等所谓乱政,造就了江南乃至大明如今首屈一指的繁华之地,试问,此新政,乱在何处!”
朱瞻墉一番话,再度震撼朝堂上下。满朝文武皆瞠目结舌,朱高炽亦不例外。
金陵!新政早已实施,他们竟一无所知!且朱瞻墉言金陵已有五百万人口,且人人皆有读书经历,此乃何等景象?京师人口几何,至多不过二百万,金陵竟是京师的两倍有余。
且金陵百姓,皆识文断字。
朝堂之上,官员们的思绪瞬间纷乱如麻。
大明读书人几何?至多不过二三十万,且水平参差不齐,能识字者便被视为读书人。
而金陵一地,读书人数量竟是大明的十几倍乃至二十倍,此乃何等骇人之事。
有人难以置信,当即提出质疑。
“殿下,即便戏言,亦需有度。微臣不否认金陵之繁华,然金陵再繁华,何以有五百万读书人?”
“微臣亦不信,别说五百万,便是五十万读书人,微臣亦觉不可能。读书岂是易事,仅识几个大字,翻阅几卷书,便称读书人乎?殿下,是否对读书人有所误解?”
“正是,我等朝中为官之同僚,哪个不是苦读多年,甚至有者苦读十载,方有今日之成就。读书,岂是这般简单。”
朝臣不信,朱瞻墉未作回应,只淡淡环视大殿,开口道:“凡在京任职,出身金陵之官员,出列!”
话音刚落,殿中末席的十余名官员挺身而出,身形笔直,恭敬异常。
“微臣见过太子!”
十数人同时向朱瞻墉行礼,动作整齐,言语一致,纪律严明。
朱瞻墉微点头,对他们道:“尔等皆由金陵调任京师,可道朕言过其实?”
人群中,一人出列,恭敬言道:“太子并未言过其实,恰恰相反,殿下久未至金陵,所言过于保守矣。”
“金陵人口已不止五百万,应有六百五十万左右。如今金陵城已扩建三次,早已非昔日之金陵。”
“凡入金陵城之百姓,无论男女老少,皆主动求学识字。”
“故在金陵,无论男女老少,皆至少读过三五卷书,识字之事,毫无问题。”
“且这只是金陵城内之百姓,尚有众多渴望入城谋生者,因未能达进城条件,只得在城外栖身,直至满足入城标准。”
“而入城之标准,便是必须读过三卷书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