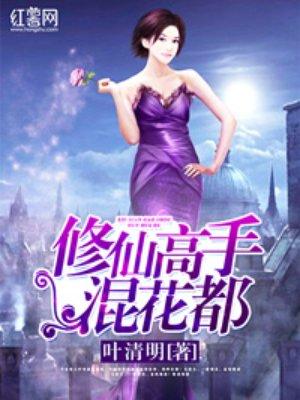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地下珠峰是啥 > 第66章 卡钻不前(第1页)
第66章 卡钻不前(第1页)
垡片刻后,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孙院士,我觉得这里面关于应力分析的部分,我们可以结合塔里木油田的实际地质条件,再深入研究一下,说不定能找到更准确的关联。您看,这里提到的应力变化模型,在塔里木那种特殊的地层结构下,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孙晓宇赞同地点点头,眼中满是欣赏,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英雄所见略同啊,小杨。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得赶紧把这个思路理清楚。时间不等人,油田的勘探工作还等着我们的研究成果呢。”
两人随即围绕这个话题热烈地讨论起来。他们一会儿在纸上写写画画,勾勒出地质构造的草图,那草图上的线条就像他们探索的轨迹,虽然曲折,但充满希望;一会儿又对着资料争论某个数据的准确性,争得面红耳赤。
孙晓宇激动地站起身,拿着笔在草图上指指点点,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你看,这个区域的应力变化,如果按照我们的推测,应该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这里的曲线走向很关键。”
杨德欢也站起身,身体前倾,凑近草图,补充道:“但是这里还需要考虑到塔里木油田独特的地层结构,可能会对这个趋势产生影响。比如这片区域的岩石成分特殊,它的抗压性和柔韧性和其他地方不同,肯定会改变应力的传导方向。”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房间里,韩国强也一头扎进了数据堆里。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像一张被红丝密密麻麻缠绕的网,疲惫不堪却又透着一股坚定。
可他依旧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那些数据就像一群调皮的孩子,总是不肯乖乖听话。他的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敲击,发出急促的声响,记录着每一个关键的数据和分析结果。
“一定要吃透这个理论,为勘探工作寻得新的突破口。”他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这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是支撑他在这枯燥的数据海洋中不断前行的灯塔。
每一次遇到数据异常,他脸上的肌肉都跟着紧绷起来,嘴里小声嘟囔着:“这里肯定有什么关键信息被我们忽略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杨德欢在与孙晓宇讨论完后,也迅速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任务中。
孙晓宇仔细地对比着不同区域的地质勘探图,眼神坚定而专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有时候,为了确定一个地质特征的标注,他会反复查阅多份资料,嘴里还念念有词:“这个标注一定要准确,它可能关系到整个研究的方向。一步错,步步错,绝对不能马虎。”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黑暗将整个油田营地笼罩。油田的营地一片寂静,只有孙晓宇和杨德欢所在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孙晓宇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发出“咔咔”的声响。他看向窗外的夜色,感慨道:“时间过得真快啊,希望我们的努力能早日有成果。这片油田承载着太多人的期望,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
杨德欢也站起身,走到窗边,与孙晓宇并肩而立。他望着窗外那无尽的黑暗,眼神中却充满了希望:“孙院士,有您的带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塔里木油田的未来,就靠我们这一次的突破了。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一定要坚持下去。”
然而,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在实际勘探过程中,接踵而至的难题让大家应接不暇。盐膏层的塑性变形极为复杂,就像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魔方,导致地质构造变幻莫测,根本难以准确预测。
有一次,孙晓宇和杨德欢一起去勘探现场查看情况。现场的风沙依旧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他们艰难地走到仪器前,看着仪器上不断跳动却又毫无规律的数据,孙晓宇的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死结,他的心里充满了疑惑和担忧:“这盐膏层的变化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复杂,我们的理论模型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这些数据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杨德欢也神色凝重地点点头,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不屈:“是啊,看来我们还得回去重新梳理思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这些数据。”
尽管困难重重,但孙晓宇和杨德欢并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他们回到办公室后,又继续投入到紧张的研究工作中。孙晓宇重新翻开那些已经被他翻得有些破旧的资料,每一页都像是他的老朋友,熟悉而又亲切。
他嘴里喃喃自语:“一定还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我就不信找不到那关键的线索。我一定要把这个难题攻克。”
杨德欢坐在电脑前,不断地调整着数据分析的模型,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细节。
“这盐膏层就像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一次勘探失败后,丛鑫龙气愤地将手中的工具扔在地上,满脸沮丧,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我们的勘探设备根本无法精准探测到地下构造的变化,这可如何是好?”说着,还狠狠地踢了一脚旁边的石头,宣泄着心中的不满和无奈。
队员们顿时陷入了沉默,帐篷内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孙晓宇院士却神色镇定,不慌不忙。他蹲下身,捡起地上的工具,递还给丛鑫龙,温和地说道:“小伙子,别灰心。困难只是暂时的,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之道。”说完,他便陷入了沉思,脑海中不断翻腾着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