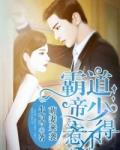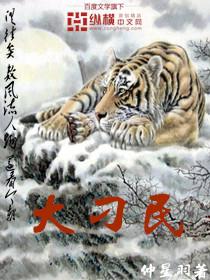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可怕的山西人作者是谁 > 第三章 团结一致共同壮大(第2页)
第三章 团结一致共同壮大(第2页)
会馆不仅仅是晋商交流商业情报的地方,更是在外地经商的晋商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场所。由于关羽是晋商心目中“信、义”的象征,所以他们即以关圣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圣的“信”来取信于顾客,摒弃欺诈、伪劣等行为。山西会馆作为同乡人的组织,凡逢年过节,同乡人常常在会馆欢聚一堂,聚餐演戏,有时在商业活动中取得重大胜利时,也举办酬神和演戏活动。晋商成员以共同的精神支柱来团结与规范晋帮成员,从而形成了一种“拟家族”式的忠减意识和巢体主义观念,进而捣成重义务、重责任、牢固和谐的商帮内部关系。
会馆在晋商中的作用还有现代商业行会的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起到了维护山西帮团队利益的重要作用。
一是组织市场公平交易。晋商行会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不仅是因为山西商人做生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是行会取信政府,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的必须,故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
二是整理货币维护经济秩序。清朝末年,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归化城一带到光绪年间,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有威信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取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牌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
三是处理商务纠纷。山西商人在外经营,不可避免会发生与行内、行外之间的业务纠纷,对此,商人行会有调解与仲裁的义务及权利。归化城马王社是同城马车业者的行会,因成立较早,社规废驰,外来车业者与会员勾结,抢劫乘客财物之事屡屡发生。1909年(清宣统元年)萨拉齐车业者来归化城后,与会首王玉柱勾结,胡作非为,会员忍无可忍,向当局起诉,经官方调查,罚外来车业者与王玉柱分别向马王社缴纳衮灯一对和挂灯一对,并向会员赔情道歉。对此事行会刻石于海窟龙王庙内,无论外来者还是本会会员都必须恪守社规,以维护本行会会员的利益。
四是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本是政府的任务,晋商行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内蒙包头,原是个村子,后来包头城市发展了,但长期没有政府办事机构。直到清末,仍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民国初年也只由萨拉齐县巡警分设了一个驻所。此时包头商民五六万人,社会治安基本是由商业行会和农民的“农圃社”维持街面。直到包头建县以前,一直是大行出代表四人,农圃社出代表一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内办公。受萨拉齐厅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各种事务,大行基本代替了行政机构。当然,这也许是一个特例。但行会参与地方政事,协助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无疑是积极的。
晋商信守“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互周互济”,更相信群体的辉煌既有天时、地利,更来自于人和。他们是保持我们民族传统美德最多的商帮,现代商人也应继承和发扬光大这种美德,它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对于一个健康的现代企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具有优秀素质的团队成员,拥有这些人才会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要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使企业成员形成为了企业的利益和目标相互协作、尽心尽力的意愿和作风,保持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统一从而实现组织高效率运作的理想工作状态。
4.联合经营,变弱为强
明人沈思孝说:“(晋商)其合伙而商者名日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有大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焉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
沈思孝的话还表明平阳、泽州、潞安等地的晋商资力雄厚,非有数十万两银不称富商。他们一般是吸收品行端正的人做伙计,并由他们出资,把经营业务委托几个伙计去办的。伙计对出资者也忠实地履行职责。如祖父辈做伙计时借得钱未还,则由子孙辈负责偿还,并以此形成风尚。因此,出资者争着要讲信义的人做伙计,念其对故人之事尚且不忘,更不会在人活着的时候昧良心。这样出资在前,获利在后;有资本和无资本的,都得益。且富者把资本尽托付各个伙计,所以估人资产的,只计算其有多少伙计,便知其有数十万或百万资产。
商人的使命在于互通有无,商人的生活就是浪迹天涯。但是江湖险恶,路途坎坷,世路与商界的残酷,需要商人组织起来。而在一个共同经营的团体中,不以信义为本,肝胆相见,组织尚难维持,何论共谋厚利。“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显示出晋商的豁达大度、识高见远。
比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最初是由三个肩挑小贩合伙创立的。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三个人虽然都没有什么资产,但是经过他们的苦心经营,逐渐有所积累,规模开始越做越大。即使后来他们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却仍然保持着联合经营的方式,并没有因为赚了点儿钱就想着各自分开经营。
当然,独立经营相对于联合经营,也有它的优点。比如在管理上,可以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有非常大的决策权,可以自由调配资源,经营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比较灵活。
但是,独立经营,必然会受到资源的限制,不管是资产也好,还是人力也好,独立经营的企业,其竞争力不强,难以与规模较大的联合企业相抗衡。
所以晋商要想突破自身局限,尽可能地获取各种资源,减少成本,扩大规模,扩大竞争力,相应地扩大利润额,就必须与别人实行某种联合互助。这可以说是扩大商业规模,形成商业航母的必然之路。
那么晋商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联合呢?
(1)建立行会
晋商在各地建立行会,以地域为单位,进行行会的划分。这种行会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统一商业规则,分享商业信息,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商业互助。信息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此彼此分享商业信息,对晋商的商业经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商业活动必然伴随着竞争和风险。为在竞争中获胜,减少和化解风险,加强自身力量,山西商人内部出现了最初的组合形式——行帮。
据《长芦盐法志》记载:“明初,分商之纲者五,日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日泽潞之纲,日平阳之纲,日蒲州之纲”。所谓“纲”,就是早期的一种商行形式。
明代长芦盐商的五纲中,山西商人就占了四纲,另外一纲为宣府之纲,也多为山西籍商人。商行是一种松散的联合方式,其行会下的各个商号,都是独立的经营实体。但是一旦大家面对共同的利益或者竞争对手,就会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形成较强的合力,对外产生较大的声势。
这种联合经营方式的主要功能是对内联乡谊,对外增强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在商业谈判中增加谈判的砝码,获取主动地位,从而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
嘉庆十九年(1814),当地税收部门非法提高对潞泽梭布商人的税收,引起山西商人的不满。潞泽会馆于是以商团的名义告到官府,一年后,经过几番周折,终于胜诉,税收获得减免。
(2)合资建立商号
在晋商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共同投入资本,共同经营,按资本的多少分取利润。投入的资本既可以是货币资本,也可以是货物、房屋门面、铺底字号等实物资本。
比如清朝咸丰年间,有个叫王吉成的山西汾阳人,以贩卖珠宝玉器为业。他结识了一位专门给皇帝梳辫子的“梳刘”,‘梳刘’因为侍候皇帝,存了一些钱,因此想拿出来做买卖。两人一商量,决定合伙创办一个绸布庄,双方投入的都是货币资本。
又比如:清朝嘉庆元年时(1796),有黄仁等三人合伙设立煤铺,其合同中写道:“立合同人黄仁,阜成门外北驴市口路东原有煤铺一座,家伙俱全,门面三间。因无力承办,情愿与张宜恩、林维乔三人合伙”。从合同中可以看出,黄仁是投入铺面等实物资本与张、林合伙。合同还规定了煤铺利润的分成办法是“黄仁三成,林维乔三成,张宜恩四成”。合同还规定了煤铺的最终控制权:以后除非张、林不做了,否则黄仁不能中途要回铺面。
再如:乾隆十二年(1815),右玉县贾又库,与本县人王厚、郭尧三人共出本银,在归化城开设“三义号”绸缎杂货铺。其资本运营的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合资共营式。
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李步安、傅德共出银6500两,董禹出银4000两,陕西人徐子健出银两千两,合银14000两,去阿克苏买玉石1000斤,然后,6月份由傅德同董禹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
以上例子说明,合资运营的方式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相当常见。
晋商合资经营的方式,大多应用于典当、钱庄、票号等金融行业,这是因为金融行业对资本的规模要求较高。经营这些行业,需要非常大的投资,因此单个商人往往无力承担,而金融行业的高额利润又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之间进行资本联合是其必然采取的方法。
在包头城,由晋商开设的“兴盛号“、”兴隆永”、“天兴恒”等钱庄,都是通过合资方式建立的。很多有闲钱的官僚在看到钱庄、票号的巨额利润后,也纷纷与人合资开设钱庄和票号。
合资制,把大家的资本集中起来,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有利于个体商人克服资金上的难题,获得更多的商机。
合资经营的合作方式,把各人的资本进行调配组合,雄厚的资金成为商业活动中保证信誉的坚强后盾,它向客户或顾客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是大企业,资本的输出或产品的质量绝对有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和卖方的交易过程就更快捷,交易额也更大,同时价格上也能更优惠。
联合经营使晋商的商号、票号具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在同业竞争中就能凭借其雄厚的资本,获取更大的主动权,甚至进行垄断贸易。
(3)人资联合
所谓人资联合,即人力和资本的联合。晋商各大商号常常是一家或几家拿出资本,由大掌柜负责经营,这种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合作方式,其实就是一种人力和资本相合作的方式。商号在各地的分号,同样也是人资联合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