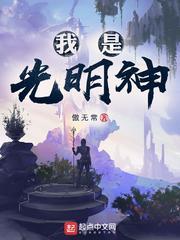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三国箱子里的皇城 > 第八十六章 飞白书(第5页)
第八十六章 飞白书(第5页)
最后被不断同化和消解一样,“飞白书”最终走上了三条品格不一的道路。
1、成了书法的一种特殊笔法丝丝露白的飞白笔法,
至今还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篆隶揩行草书体中,使书法的笔法逐渐丰富起来,
酝酿出了诸如“润含春雨,燥烈秋风”的意境。
对此,宋代的姜夔在《续书谱·总论》中就说“真行草书之法,
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而且进一步肯定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
因为飞白墨色的轻细,在客观上就增强书法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这在行草书中尤其突出。
2、成了国画的一种特殊技法
关于飞白用于绘画的记载,恐怕最早就是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篇》中,
顾恺之为殷仲堪画像的记载。原文是“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像。
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瞳子,
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敝日’”。
这说明,远在两晋时代,飞白不仅专用于书,而且已经转入绘画成为一种特殊的技法。
后来,宋末元初的赵孟頫也有“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的诗句,
并且,在宋人不断完善的皴擦技法中,我们更易看到飞白的迹象。
比如苏轼的《枯木竹石图》即是一例,尤其是在宋、元、明、清滥觞的文人画中,
飞白技法可谓俯拾皆是。
3、成了一种民间工艺
如果说飞白以上二途,虽然被消解和弱化,但还保持了一定品位的话。
那么,它的第三条道路却是滑落民间,走向了低俗。
“飞白书”虽然品位不高,但它的杂耍性质和工艺性质,会使广大人民非常喜爱。
当皇朝士宦对它嗤之以鼻之后,她就如被贬出宫的嫔妃一样,
虽失宠于朝廷,但在民间却大受欢迎。而今,我们在庙会或有些民间乡场,
依然可以看到那些被称为“鸟虫书”或“花鸟字”的民间艺术。
而它们正是有“飞白书”的明显胎记的嫡系传物。
无论是书法的飞白笔法,还是绘画的飞白技法,以及胎息飞白的民间书画,
都有力地说明:“飞白书”并未消亡,而只是转变成了其他的东西而残存在中国艺术史上。
对“飞白书”的兴衰及其走向的研究,弥补了书体个案研究的某些空白,
使我们弄清了相关史学和美学问题,知道了它的兴衰原因,
认定了“飞白书”的美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了解了“飞白书”的最终走向,
有利于当今书法的创作和借鉴。
喜欢三国:箱子里的皇城请大家收藏:(www。aiquwx。com)三国:箱子里的皇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