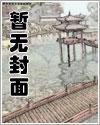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人生几何 > 第二辑 时光留痕(第2页)
第二辑 时光留痕(第2页)
要逮到这样一只好蛐蛐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到秋天,男孩子便四处寻觅,白天钻草丛翻石头,旮旯拐角到处找,有时也能抓到几只。但要逮到好蛐蛐,则要到晚上,尤其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好蛐蛐才会鸣叫。夜里逮蛐蛐,手电筒是必不可少的,再拿用过的作业本叠几个装蛐蛐的纸筒,折几根扫帚子就齐了。到了晚上,全院的人都睡了,因为心里有事,我躺在床上,告诉自己千万不能睡着,如果睡着了,今晚的行动就前功尽弃了。就这样撑到半夜,听着院里蛐蛐此起彼伏的鸣叫,想着父母一定睡着了,便悄悄地爬起来,揣好准备的工具,蹑手蹑脚,轻轻拉开门闩,双手抬着门一点一点打开,这样门枢才不会发出声音,然后回身轻轻带上门,院子里就是我的天地了。那时我分辨蛐蛐的叫声已经有经验了,大个头好蛐蛐的叫声响亮而浑厚,叫声细弱的那一定不是好蛐蛐。先循着叫声确定好目标,再慢慢靠近,等确定了位置再打开手电,顺着砖缝往里照,就见一只大个头的蛐蛐已做出攻击的姿势,叫的频率顿时快了许多,这时用扫帚子在前面一逗,蛐蛐就会向外攻击,跟着子咬出洞外,这时就是抓捕蛐蛐的最好时机,运气好的话,一晚上可以逮到三四只。记得有一次夜里在宋奶家南窗外煤堆旁逮蛐蛐,一不小心碰到了盖煤的石棉瓦,三更半夜哐当一声,吓得我赶紧埋头不敢动弹,只听屋里姜平他爸一声:“谁呀?”紧接着屋里的灯就亮了,我灵机一动,“喵”地学了一声猫叫,停了一会儿屋里灯又灭了,我这才舒了一口气,悄悄溜回家里。
抓到满意的蛐蛐是最高兴的事了,半夜没睡的付出没有白费。第二天就要给蛐蛐安家了。养蛐蛐我们都用废弃的搪瓷缸子,条件好的用瓦罐,底上铺上湿土,在上面搭一个洞,把晚上逮的蛐蛐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再放点生辣椒、瓜子仁,盖上盖儿,一个蛐蛐窝就大功告成了。最多时我的床底下放着成十个蛐蛐罐儿。逮蛐蛐养蛐蛐都是为了斗蛐蛐,院里的韩勇也痴迷玩蛐蛐,经常满世界去找蛐蛐,甚至逃学去逮蛐蛐,我就在夜里逮蛐蛐时碰到过他。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斗蛐蛐,一开始先拿出一般的蛐蛐斗,有点像擂台赛,最厉害的蛐蛐王最后才出场。看着双方的蛐蛐钳口大张,你来我往,咬扭翻腾,主人也暗自较劲,为自己的蛐蛐鼓劲加油,最终胜者振翅鸣叫,紧追不舍,败者掉头逃跑,再不敢战。胜者的主人也兴高采烈,得意扬扬,败者的主人则面上无光,暗下决心:一定要逮个更厉害的打败你!小时候自制力差,有时候就玩得影响了上课和学习,父亲曾经一气之下,把我和弟弟养的蛐蛐都喂了宋奶家的老母鸡,搪瓷罐也扔进了垃圾筐。有一天,韩勇正在家门口倒腾他的蛐蛐,他爸回来了,那天不知是老师告状了还是心情不好,到跟前一脚就把蛐蛐罐儿踢飞了,韩勇把剩下的罐子压在身下不让踢,结果被揍了一顿不说,“韩总理”还把所有的蛐蛐都踩死了。伤心的韩勇用仇恨的目光盯着他的爸爸,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过了一阵子,突然有一天,“韩总理”下班回来,进到院子就大声喊:“韩勇,韩勇,爸给你逮了个大的!”喜出望外的韩勇从此又开始玩蛐蛐了。
西安的冬天尽管很冷,孩子们却盼着下雪。那时候雪比现在多,常常是一夜大雪过后,清晨一打开屋门,眼前已是白雪皑皑的世界。覆盖着厚厚积雪的院子里、巷子中,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在雪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男孩子们滚雪球、打雪仗,滑雪溜冰,玩得不亦乐乎;女孩子则喜欢堆雪人,胡萝卜的鼻子黑煤球的眼,再做顶帽子和围巾就齐了,能让她们高兴好几天。男孩子滑雪常常把院子滑得锃亮光滑,这时宋奶就该骂我们了:“你们这些熊孩子,想摔死老太太呀!害得我几天都不敢去上厕所。”到了过年,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穿新衣、吃美食、打灯笼、放炮仗……那时候穷,买不起花炮,更不要说礼花了,男孩子缠着父母买上一串一二百响的鞭炮就欢天喜地了。回去拆开来,每天揣上几个出去,一个一个地放,从腊月小年一直要放到正月十五。小一些的孩子则喜欢打灯笼,那会儿没有花灯,都是那种竹篾子、中国红的圆灯笼。下面用萝卜穿上一支蜡烛,上面用一尺来长的竹棍挑着。天刚擦黑,小弟弟、姜平、韩卉就打着灯笼在院儿里转悠,嘴里还念念有词:“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咧回家睡……”
五
疯玩的日子过得很快,上了初中后,父母让我和大弟开始做饭干家务,并且给我俩分了工,我主要负责挑水、擀面条蒸馒头做主食,大弟学做菜炒菜。饭后洗碗,一个一、三、五,一个二、四、六,礼拜天临时指定。记得第一次蒸米饭,母亲交代我,蒸的过程中不能揭锅盖,揭了锅盖饭就夹生了。我下午四点就把米饭蒸到炉子上了,蒸了一个多小时也不敢掀锅盖,直到水烧干了,宋奶闻到了煳锅的气味,从炉子上端开锅揭开锅盖一看,竟然还是半盆大米。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对着宋奶直嚷:“我妈说了不能揭锅盖,你把锅盖揭了,米饭就熟不了啦!”宋奶说:“傻孩子,蒸米饭米里不放水怎么蒸?
不放水蒸一天也蒸不熟的。”这就是我第一次做饭的经历。
有了这次教训,我此后不论是擀面还是蒸馍烙饼,都会向宋奶请教,因为宋奶做饭可是行家里手。印象中,宋奶最会做的是面条,什么汤面、捞面、卤面,什么臊子面、猫耳朵(也就我们关中的麻食)、炸酱面,样样拿手。宋奶家的锅灶在窗外的台阶上搭着,每当她卤臊子、炒炸酱的时候,满院子都飘着香味。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桌,色香味俱全,再调上宋奶亲手酿的香醋,那真是诱人食欲,令人垂涎。我到现在都爱吃醋,就是那时受了宋奶家那种香醋的熏陶。
烙烧饼的技术是父亲教给我的。父亲用的是他自创的烙饼方法,用一个剪去底的旧脸盆做炉圈,将发面饼两边先在凹锅里烙上花,再靠在锅下的炉圈上烤,待凹锅里的饼烙得差不多了,锅下的饼也烤熟了。这样烙出来的饼又暄又酥,皮脆里软,散发着淡淡的麦香,十分好吃。
贪玩是孩子的天性,常常玩得下午父母快下班回来了,还没有开火做饭,甚至中午的碗筷都没有洗。于是赶紧跑回家,把中午的碗筷泡到盆子里,塞到柜子下面或床底下藏起来,失急慌忙地打开炉门扇火做饭,待吃完晚饭后,再把中午的碗筷悄悄端出来一块儿洗。那时为了省煤,炉子不用时就要封着,小君家和宋奶家用煤很省,每天两三块蜂窝煤就够了,而我们家每天四五块还不够,母亲便让我们向他们两家学习,节约用煤。学习的结果就是炉子经常被封灭了,早上起床劈柴生炉子成了家常便饭。
在屋里憋屈了一个冬天,开春天刚一变暖,各家便纷纷搬到院里吃饭,一家人坐着小板凳,围着小饭桌享用晚餐。宋奶家拿手的是保定府菜;,小君家善烹淮扬菜;我母亲是湖南人,做的是湘菜,辣味居多;韩勇他妈是湖北人,做的多是湖北菜。各家的餐桌上都各显特色。俗话说,吃饭穿衣量家当,每到吃饭的时候,谁家的饭味道香,菜里面有肉,都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那时候年龄小,总觉得别人家的饭好吃,希望母亲也能做出像别人家一样的饭菜。如果做了好菜,男主人则会从屋里摸出一瓶酒来,小酌几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饭馆里已经有卖散啤酒的了。记得一个礼拜天,父亲用暖水瓶买回一暖瓶啤酒,邀请姜平他爸尝尝。那时啤酒是稀罕物,俩人都小口小口地品酌,不像现在喝啤酒咕咚咕咚地牛饮。我也尝了一小口父亲杯子里的啤酒,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连忙吐了,问父亲:“什么味道呀这么难喝?”父亲笑着说:“马尿的味道,小孩不能喝。”
吃饭时,也是邻居们家长里短谝闲传的时候。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谝得最多的是哪儿的菜便宜,哪儿卖的肉膘厚,哪个商店里处理布头了……印象深的是聊谁家为啥都生男孩,谁家又都是女娃。谭妈说生男生女有秘方,用什么方子可以生男娃,什么办法能生出女娃来。韩勇他家儿女都有,于是大家都让“韩总理”介绍经验。正端着饭碗,圪蹴在台阶上的“韩总理”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刚要说话,却好像被一口饭噎住了,只见他脖子一抻一抻努力做吞咽状,眼睛向上一翻一翻的,待咽下这口饭才说出话来:“哪有什么……方子,俺是瞎猫逮死耗子,冒碰的。”听得大人们哈哈大笑。我那时小,听不太懂大人们的话,也跟着傻笑。不知怎么的,打那以后,“韩总理”吃饭就落下了抻脖子翻眼睛的毛病。
那个时候普通居民每个月只有四两油、二十七斤半粮,其中四成是杂粮。买肉、鸡蛋、糖、布、煤、肥皂,甚至买火柴、碱面都要凭票凭本。排队购物司空见惯,特别是到了过年跟前更是清晨四五点钟就得拿着小凳子到肉店菜店门口去排队。菜是限量供应的,一个人可买几斤菜都是提前公布了的,常能看到一家老小几个人一起排队买菜的。那时候肉越肥等级越高,四指厚的膘是一级肉,九毛多一斤;三指厚的是二级肉,八毛多一斤;三指以下的是三级,七毛多一斤。那时候人缺油水,每次母亲都把肥肉切下来炼成大油,放在一个黑瓷盆里炒菜用。如果能买到猪头猪下水,那这个年的餐桌就丰富了。粮店在通济中坊东头北侧的院子里,每次买粮都要拿着粮本,提着面袋子,有时细粮粗粮中间用绳扎了装在一个面袋里。冬天天不亮就到粮店排队买红苕,红苕两分钱一斤,一斤杂粮可换五斤红苕,为的是能让孩子吃饱肚子。买煤就更麻烦了,让人送是要花钱的,为了省点钱常常都是自己去煤店拉,先得四处借架子车或三轮车,然后排队交钱装煤。拉回来车子进不了院,要把煤从大门口搬到厨房一块块码好,这对一个十四五岁、身单力薄的孩子来说,劳动强度是可想而知的。好在那时年少不惜力,睡一觉就没事咧。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兄弟仨,肚子似乎老是饿着。有一天疯玩回来,肚子很饿,我就在屋里到处翻找吃的,发现床下一个砂锅里有几个鸡蛋,赶紧煮了一个,不等放凉就迫不及待地剥皮,刚一剥开却发现里面是黑的,于是又煮了一个剥开还是黑的,想着鸡蛋肯定是坏了,便扔到了垃圾筐里。过了几天母亲问砂锅里的变蛋怎么少了,我连忙说鸡蛋都黑了坏了,我扔了两个。母亲看着我,又生气又好笑,说:“变蛋就是黑的,要留着过年吃的,你就给扔了?”打那以后,母亲就把变蛋锁在了柜子里。那时候自己能吃得起的零食就是一分钱一颗的水果糖了,兜里揣着几分钱,到北大街的中华食品店,盯着玻璃罐里花花绿绿的水果糖,买上几颗藏在口袋里,能甜上好几天。吃完了玻璃糖纸舍不得扔,把它抹平了夹在书本里,过一阵打开捧在手心,看着两边翘起的糖纸,心里也甜丝丝的。
老是粗茶淡饭的我们仨,如果父母能带着在街上吃点东西,那就是幸福无比的事了。记得一个夏天的傍晚,饭后父亲带着我们散步,经过北大街路西侧的“新中华甜食店”(“文革”后期恢复为“梁记甜食店”),那天父亲高兴,带我们进去,花了一毛五给我们仨一人买了碗醪糟。还想吃店里的元宵,然而没有如愿,但喝着甜甜的醪糟,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后来母亲还带我们在这家店吃过冰激凌。印象最深的是二府街口路北的那家“粉汤羊血泡馍馆”。靠路边的门面里,支着一口三尺大锅,里面沸腾着香气缭绕的调料浓汤,厨师将一块块羊血切成三寸来长、筷子粗细的形状,码在案板上,再把豆腐切成一寸见方的薄块备用。食客买上两个烧饼,再花一毛五买一份羊血票就可以掰馍了。烧饼是半发面的,不能掰得太大也不能太小,掰成指头蛋大小刚好,掰好后交到炉头上就等着美食了。只见冒馍的大厨撕一撮粉丝,码上切好的羊血和豆腐在馍碗里,用铁勺将锅里翻滚的浓汤浇在馍碗里,压两下再滗出去,如此反复几遍,再浇上明油和油泼辣子,最后加上汤,撒上香菜,一碗红油亮亮、香味扑鼻的羊血泡馍就做好了,那时觉得这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了。还有一种印象深的美食就是北大街“代代红饭馆”的“一窝丝”油塔了。父亲曾经买回来过,吃的时候用筷子夹住抖一抖,就成一窝丝了,蘸上蒜泥送入口中,那真是人间美味呀!尽管那时穷,这些美食都很少吃,但那种味道却深深地留在了记忆中。
六
我上小学六年级那年,门房的谭妈得了一种怪病。先是膝盖疼,过了一阵脚、胳膊和手上的关节也开始疼,而且病情发展很快,后来连走路都困难了。到医院治疗也不见好转,辗转了多家医院才确诊为类风湿关节炎。刚开始的一两年还能拄着拐勉强走路移动,尽管吃了不少药,但病情还是不断加重。到了1972年,腿上和手上的关节都变形了,最后彻底走不了路,只能卧床了。这下可苦了小君,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父亲在铜川工作,每天除了上学,还要照顾卧床的妈妈,既要做饭干家务,还要给妈妈翻身洗澡倒尿盆,一直坚持了很多年,真是不容易呀!
20世纪70年代初,上房的李桐青娶妻结婚了。可能因为家里成分不好,结婚没有办什么仪式。新娘子是西五路一家副食商场的会计,名叫王怡,后来我们都叫她王姨。结婚后的桐青工作更努力了,每天早上穿着工作服,从屋里推出他那辆大链盒自行车,转铃一响,踩上脚蹬子,从上房溜到门房,车把一抬座一出了院子,动作利落而潇洒。记忆中,和桐青打交道最多的是我上高中时自己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的那段时间。那一阵我对此十分着迷,先从装矿石收音机开始,从无线电商店买了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线圈、电路板等零件,然后按照无线电杂志上的电路图安装。因为家里没有电烙铁,所以每次焊电路都要到桐青屋里去焊,他也很乐意指导我。尽管最终也没能装成一部像样的收音机,但我当时觉得他是我们院里学问最高的人,有什么问题都愿意向他请教。结婚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民民。又过了两年,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名叫欣欣,这两个孩子成了我们这个院里的新生代。
那个时候,后院的林增太也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我们都搞不清他在哪里工作,但他三天两头地带回女朋友来,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剪发头的、扎辫子的,穿布拉吉的、穿的确良的,过几天就换一个,但只见开花不见结果。而增太却把原因归咎为没有结婚的房子,缺少相处的空间。于是,每次他带女朋友来家,父母都把他弟弟妹妹撵出门,老两口也出去溜达,给儿子腾出空间。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他弟弟增智不愿意出去,老爷子很生气,看着流着鼻涕的小儿子,用河南话骂道:“恁大的孩儿了,成天吸溜吸溜,你就不会哼哧一擤!”
越骂越气,一巴掌扇过去,只听啪的一声,增智的鼻涕从鼻孔里一下子甩到了额头上,捂脸哭着跑了。
大约是1973年吧,从南泥湾五七干校回来的父亲,由于靠边站加之身体不太好,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这期间父亲给家里干了一件大事。父亲和母亲结婚二十年,搬了多次家,但家里一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利用这段时间,父亲买木材,找木匠,做了大立柜、半截柜、写字台、方桌、床头等几件纯木家具。但在漆家具时却出了意外。油漆的师傅姓焦,因为是冬天,怕油漆上冻,便把家具搬到屋里刷漆,又生上煤炉提高温度。干了一天活的焦师傅到了吃晚饭时,出现了头晕、恶心、气短的症状,原想可能是干活累的,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歇了一阵症状仍不见轻,急忙送到医院,一检查是煤气中毒,连夜住了院,打针吸氧,住了三天才恢复,后来再也不敢在屋里放炉子了。祸不单行,家具做完后没有多久,父亲就在北大街被自行车撞了,撞倒在地的父亲头磕在了路沿上,人当时就昏了过去。当我们接到百货公司的电话赶到西医二院时,父亲还没有醒过来,撞人者已经跑了,父亲是被好心的路人送到医院的。医生说是比较严重的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最终在医院住了十几天才回家。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按照政策,我是要上山下乡的。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自食其力,为父母减轻点负担。
在等待下乡的日子里,我和儿时的伙伴丁成,到药王洞一家针织厂去干了几个月的临时工,一个月能挣十几元钱。这是一家莲湖区的集体企业,女工居多,干的活主要是用半手工半自动的机器织毛衣。活多时工厂里要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我们这些临时工都被安排上夜班。十七八岁的孩子,一到半夜就困得不行,常常中间吃饭时,丁成就睡着了。一些喜欢搞恶作剧的姐姐就在他脸上涂抹上机器上的黑油,待叫醒他进车间去干活时,女工们便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经常是早上下班换工装时,才发现自己脸上的黑油。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们俩骑着二八自行车,在清晨空旷的大街上,迎着朝阳,双手撒把,高唱革命歌曲,颇有些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豪情。
我是1976年1月8号下乡的,临行的前一天,母亲为我准备好了行装。一只父母用了多年的帆布箱子,装了衣服鞋袜,还有碗筷和洗漱用具,再加上铺盖卷,就是我全部的行李了。头一天,我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水,为父母和弟弟做了最后一顿晚餐。看着生活了十年多的四合院,真有点恋恋不舍。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熟悉,在这里自己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即将踏入社会的高中毕业生,这里留下了我很多的记忆,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七
这一走,果然再也没能回去。我下乡的那一年,我们家就搬走了,离开了居住生活了近十一年的通济南坊十五号。我后来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忙忙碌碌,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四合院。为了写这篇回忆,几经打听,找到了年届六旬的谭君,向她询问了一些我们家搬走后院儿里的情形。谭君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如今老两口和儿子一块儿生活,花甲之年的她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小君的影子,说话慢条斯理,轻声细语,娓娓道来。
她告诉我,“文革”结束后,大概是1978年,政府给上房的李广魁老爷子落实了政策,返还了“文革”中收缴的那间房子和部分物品,老两口又从河南回到了院里,和儿子桐青生活在一起。民民和欣欣20世纪90年代中期先后下海去了珠三角。李家的小毛生活不太如意,结婚不久又离婚,至今孑然一身。并且在“文革”中因偷听敌台失去了工作,后来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有人在西仓的档子上见过他卖过鸽子和鸟食。
“韩总理”他家腾了房子,搬到了糖坊街一个小区里。两个儿子不甚争气,韩勇后来竟吸上了毒品,被关进了戒毒所;韩琪上高中时在一次打群架中用刀捅人致死,被判刑坐牢;只有韩卉是两口子的安慰,据说她和丈夫90年代去了美国,开了一家中餐馆,现在居住生活在美国,已拿到了绿卡。如今年届八旬的王金秀和大儿子生活在一起,戒了毒的韩勇对母亲倒是很孝顺。“韩总理”于1992年因肺气肿去世。谭伯1980年退休回到了西安,1987年因脑溢血去世。
1986年,通济坊被拆迁改造了,三条巷子所有的四合院被拆得一个不剩。我90年代初专程去探访过,故地重游,已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景象,只有中坊的那个菜店还顽强地屹立着。一幢幢火柴盒般的砖混楼,挤挤挨挨地簇拥着,家家户户的窗子和阳台都被防盗网罩着,邻居们生疏而不相往来,没有了往日四合院那种和谐与安详。拆迁时,补偿给上房李家三套住宅,老爷子自己住了一套,给两个儿子各一套。谭君家被安置到北门外铁道边的一个小区,在每天轰隆隆的火车声中,被病痛折磨了三十九年的谭妈,于2010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姜平家则搬到了青年路的一个四合院中,姜玉昌走在了宋奶的前面,姜平接了父母的班,在邮电局工作,宋奶一直活到九十八岁无疾而终。只有后院的林家拆迁后不知所终。
我们的上一辈陆续都辞世了,而我们的下一代对四合院则完全没有概念。如今四合院是越来越少了,写这篇文字的目的,就是想让四合院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让下一代对四合院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