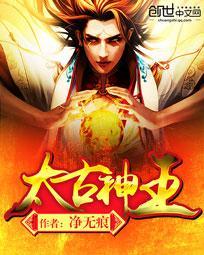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走出至暗时刻的能力更重要 > 第十三章 新的生活(第3页)
第十三章 新的生活(第3页)
1982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屋里爬格子,忽听有人问话:“这是贺绪林的家吗?”我抬头一看,屋门口站着一位陌生的中年人,含笑看着我。我疑惑地看着他,点了一下头。他笑着说:“我是商子雍,给你写过信。”说着,他伸出手向我走来。我急忙握住他的手,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傻笑。
商老师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戴着眼镜,中等身材,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一身的书卷气。商老师说,编辑部委托他来看看我,并告诉我,我的两篇小说将在第12期《长安》杂志上刊发。我惊喜万分。我的作品终于登上了正儿八经的文学刊物,一个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跋涉的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一时激动无语,只是紧紧地握着商老师的手。
商老师详细地询问了我受伤致残的经过及现时的处境,我一一作答。
他热情地鼓励我,中肯地指出我创作上的得失,并殷切地告诫我要坚持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
1982年年底我收到了第12期《长安》杂志,上面不仅刊发了我的两篇小说,还刊载了商老师一篇介绍我的文章——《在逆境中奋飞》。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刊物,我真想大声呼喊,可嗓子眼发涩,只觉得眼睛发潮……
我似乎看到一颗流星从天上划过,黑沉沉的夜幕上闪过一道亮光。
时隔不久,商老师又写了篇介绍我的文章——《贺绪林素描》,发表在1984年第4期《陕西青年》上,向社会介绍我。
后来,在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陕西省文联)和陕西省作协召开的几次创作会上,我都见到了商老师。每次见面,商老师都给予我热情的鼓励。
1998年冬季,陕西电视台《周末俱乐部》栏目“文坛光点”版块为我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制作节目之前,编导魏含章来家采访我,问及在创作上谁都对我有过帮助,我说到了商老师和赵熙老师。再后,魏编导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将聘请商老师做此次节目的嘉宾主持。得知此消息,我十分高兴。
制作节目时,我又一次见到了商老师。商老师一点儿也不显老,依然风度翩翩。更让我感到惊奇和敬佩的是,在摄像机前商老师侃侃而谈,声情并茂,挥洒自如,再次把我介绍给更多的观众和读者,那水平完全可以与电视台知名主持人相媲美。
回首往事,我有说不出的辛酸和苦恼,也有道不尽的欢欣和喜悦,但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我在人生的路口徘徊之时,是商老师最先向我伸出援手,扶我上战马,使我下定决心在文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为此,我常怀感恩之心。
2010年,在“陕西著名作家走进杨凌”的采风活动中,我有幸忝列采风团中,再次见到了商老师。他步履稳健,红光满面,精神矍铄,风度不减当年,完全不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闲谈中,我提到他过去对我的帮助,他淡然一笑,说道:“那是一个文学编辑的职责,也是应该做的事,不值一提。”话虽是这么说,可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两天的采风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分手时商老师握着我的手关切地叮嘱,要我多保重身体。我又一次被感动了。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商老师笔力遒健,宝刀不老,健康长寿!
五
1982年秋季,我写了一部反映残障人同疾病抗争的中篇小说《生活之树常绿》,四万余字。写完后我很茫然,不知该往哪家刊物投稿。是时,我手头恰有一本新出的《当代》杂志,顺手查出地址,便贸然寄出。
半年过去,没有消息。我以为稿子寄丢了,要不就是又被“枪毙”
了。就在我完全丧失希望之时,乡邮递员送来一封北京的挂号信件。我一瞧是大信封,知道又是退稿,心里顿时拔凉拔凉的。大信封被我扔在桌子上,我都不敢去看,抱着头坐在桌前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我把手伸向了信封。不管咋的也得看看呀。
我慢慢拆开信封,果然是退稿,但附着一封长信。我急忙看信,第一遍竟然没看明白。我又慢慢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激动兴奋得心跳如鼓。信中对我的习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嫌不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让我修改之后尽快寄去。信尾署名:《当代》编辑部。
我欣喜若狂,深深地呼了一口气,那一刻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刻不容缓,我当即按照编辑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动笔改稿。三天改完,我立即寄出。半个月过后,我又收到退稿及信件,信中说,改稿虽有进步,但并不理想,并再三告诫:认真修改,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从笔迹看,两封信出于同一人之手。
怎样才能改得令编辑满意?我心中茫然,无从下笔。文路崎岖,无人指津,苦恼烦躁之中我冒昧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情况和处境,请求编辑部能派位老师来帮我改稿。信寄出后,我就为自己荒唐的想法而后悔。这样非分的要求编辑部怎么能答应!
万万没有想到,两周后,《当代》编辑部的何启治老师突然来到我家。
那是1983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艳阳高照,天气燥热。我正在午休,乡友喊我,说是有人找我。我刚坐起身,两位中年人就进了家门。其中一位是县文化馆的同志,他给我介绍:“这位是《当代》杂志的何启治老师,他是专程来看望你的。”我又惊又喜,握着何老师的手激动得连话都不会说。
何老师四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大编辑的架子。何老师说我寄给他的信他收到了,刚好他来陕西组稿,就顺便来看看我,还说编辑部的老师都向我问好。何老师又说,两封信都是他写的,稿子很有基础,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说着他拿出稿子谈起了修改意见。显然他已经把稿子看了好多遍,意见中肯而具体,且把需要修改的地方都用红笔勾画了出来。他说,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要拘泥于真人真事,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来虚构,但要虚构得合情合理……(原话我已记不大清楚,大意如此。)我茅塞顿开,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何老师起身告辞。我很想挽留他住一宿,再聆听聆听他的教诲,但我知道他是个大忙人,在西安还有许多事情要办,而且我的茅舍实在太寒碜,不便留客。
临别之时,何老师握着我的手说:“小贺,别气馁,鼓起勇气重新生活,我会尽全力帮你一把的。”我的眼睛发潮,喉咙发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紧紧地握着何老师的手……此后不久,我的中篇小说《生活之树常绿》刊发在1983年《当代》第2期增刊(《新人新作专号》)上。何老师给我寄了五本样刊,还有一沓未装订的单篇。我翻到目录,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突然想哭。万里征程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再后来,何老师陆陆续续给我寄来许多书刊,并多次写信鼓励我,希望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何老师在我最危难之时坚定了我的信念,他在我心中如同神一样地存在着。
我原本是个活泼不甘寂寞的人,伤病让我失去了自由,近十年我几乎没有迈出家中的小院。那时没有电视,更别说电脑啥的,加之农村的信息十分闭塞,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井底之蛙,头顶永远只是院子上空那片天。
我渴望有朝一日走出囚困自己的那间屋子。
《生活之树常绿》发表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稿酬——三百八十元。
活了三十年,这是我最大的一笔收入,拿钱的时候我还有点儿不相信这钱是我的。我跟嫂子商量这笔钱怎么用。我说给家里人都买件衣服吧。嫂子说:“给你买辆手摇轮椅车,我在杨陵街道上见过腿脚不便利的人坐着摇,很方便的。”我说:“我听你的。”
于是,我用这笔稿酬让在西农大工作的外甥给我买了辆手摇轮椅车。
杨陵没有货,外甥托人在西安买。外甥送来手摇轮椅车那天,一家人都很高兴,我更是无比兴奋。从那以后,我可以自己出去转一转,呼吸着家里以外的新鲜空气,见闻着家里看不到的事物。
我常常回忆起这件事,感慨万千。那时,伤残使我对生活丧失了信心,彷徨之中,创作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但成功的彼岸距我太遥远,虽然屡败屡战,但心火渐熄。倘若何老师没有来家给我鼓励,倘若没有他的扶持帮助,倘若那个中篇又被“枪毙”,我也许不会再舞文弄墨,也许我的生命早已枯萎凋零。那个中篇的发表使我在绝望之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使我生命的航船在再次搁浅之后又升起了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