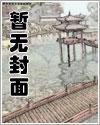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明末乱世恨女主攻略 > 第17章 博弈(第1页)
第17章 博弈(第1页)
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崇祯皇帝呈上了一份关乎万千百姓生死存亡的奏疏。
彼时的陕西,地理环境本就多有不利。广袤的土地大多呈现出硗缺之态,所谓硗缺,便是土质坚硬而贫瘠,不适宜农作物的茁壮成长。
这样的土地条件,使得百姓们在农事经营上举步维艰。他们辛勤劳作,却往往只能收获微薄的成果,难以积累起富足的生活资本。
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边疆的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北方的游牧民族屡屡犯边,朝廷为了保家卫国,不得不大量征兵。
无数的青壮男子被从田间地头强行征召入伍,背井离乡奔赴边疆战场。与此同时,庞大的军费开支也如同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了陕西百姓的肩头。
为了筹集军饷,官府不断地增加赋税征收额度,各种名目的加派纷至沓来。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原本就不富裕的民间社会,迅速陷入了绝境。
往昔热闹的村落,如今十室九空,大量的家庭因为男丁的离去和赋税的重压而破败不堪。
祸不单行,陕西又遭遇了连年的凶荒。自然灾害仿佛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所操控,接二连三地肆虐这片土地。
从最初的局部歉收,到后来的大面积灾荒,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而崇祯元年的这场灾荒,更是达到了酷烈异常的程度。
李应期在其巡历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景象。
他从凤汉兴安出发,一路经过延庆、平凉,最终抵达西安。所到之处,皆被干旱的阴影所笼罩。
自五月起,天空便吝啬地不再降下一滴雨水,这种干旱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秋季。
三伏天里,本应是农作物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然而烈日高悬,亢旱难耐,那炽热的阳光无情地烘烤着大地,将田间的禾苗一点点地烤干、烤死。
曾经绿油油、充满生机的田野,如今变成了一片赤野。大地上,青草早已枯萎,断了炊烟的村庄随处可见。
百姓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粮食来源,无奈之下,只得背井离乡,踏上逃亡之路。
在道路之上,李应期不断地看到令人心碎的场景。
灾民们数百人一群,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他们拥堵在道路两旁,看到官员的身影,便纷纷围拢上来,苦苦哀求赈济。
那一双双干枯的手,那一声声凄惨的呼喊,仿佛是对命运不公的控诉。
他们声泪俱下地诉说:粮食早已消耗殆尽,如今已断粮多日。家里年迈的老人身体本就孱弱,长时间的饥饿让他们骨瘦如柴、面色蜡黄;年幼的孩子们更是可怜,饿得面黄肌瘦,双眼无神。
而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在延安的宜、雒等地,以及西安的韩城等所属区域,社会秩序已经濒临崩溃。
由于饥饿的逼迫,一些灾民开始走上极端。他们联合起当地的回民以及一些被称为啰贼的山民,这些人或许原本也是善良的百姓,但在生死边缘的挣扎中,他们选择了铤而走险。
他们打着旗帜,敲着金锣,纠集起上百人甚至更多的人,公然在白昼进行抢掠。
他们闯入富户人家,抢夺粮食和财物,弱肉强食的悲剧不断上演。
在他们看来,与其在家中忍饥挨饿,坐以待毙,不如通过抢掠来获取一线生机,哪怕这种行为是违法乱纪,违背道德伦理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李应期深知,如果朝廷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在奏疏中言辞恳切地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请求。
他首先恳请皇帝俯念陕西灾荒的重大程度。
这绝非是局部的、轻微的灾害,而是关系到整个陕西地区的稳定,甚至关乎大明王朝根基的重大事件。
他请求皇帝敕令户部进行商议,对于天启七年拖欠的以及崇祯元年加派的按地亩征收的辽饷,应当立即予以免征。
这两项赋税的征收,已经让百姓们苦不堪言,继续征收只会将更多的百姓逼上绝路。
并且,对于本年度的赋税,也应当酌情减免一半。
如此一来,百姓们或许能够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得以在这艰难的岁月中生存下去。同时,他还提到了军饷和宗禄的问题。
这些开支虽然对于朝廷的运转和宗室的供养有着重要意义,但在当下的灾情面前,也应当一并宽缓。
毕竟,如果百姓都饿死了,军饷无人可征,宗禄也失去了来源。
若此时仍然固执地坚持征收,而不顾百姓死活,那无异于杀鸡取卵。
就算将那些饿殍在棍棒之下处死,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激起更大的民愤,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
此外,李应期还希望皇帝能够回顾历史,查考万历十一年以及十三年全陕西发生大饥荒时的应对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