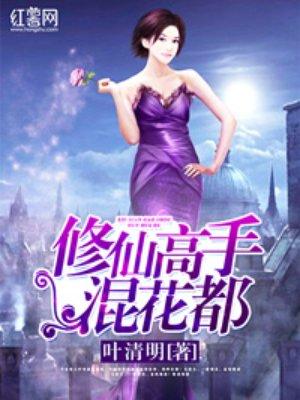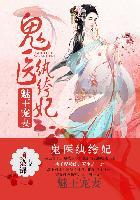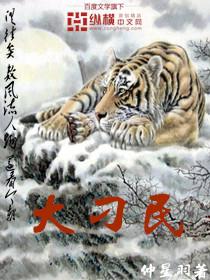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并不如烟是什么意思 > 第55章 年3月18日 香港陈伯家(第1页)
第55章 年3月18日 香港陈伯家(第1页)
第五十五章
1963年3月18日
香港
田之雄花了一个多星期就把站里的资料室整得像模像样了。他从香港左派书店买了许多大陆出版的书籍、报刊,整整齐齐地摆满几个大书架,又从逃港的人手中收集了许多各省市的粮票、油票、布票、工业券、单位介绍信、工作证甚至火车票、电影票等等实物票证,煞有介事地镶在几个大镜框里,俨然一副大搞研究的架势,丁站长看过后赞赏有加。
由于田之雄略施小计便借助黑道兄弟之手顺顺当当地找回丁站长的皮夹子,避免了泄密,加上莫之英添油加醋一通吹捧,当然略过了他和大牙被绑一段,使得丁站长更对田之雄刮目相看,不仅给他住处装了电话,原先有的几分戒心也少了许多。这使得田之雄以各种借口外出自由了很多,只是田佩瑜多少有些酸溜溜的。
这两天他正着手写一篇关于广州洪门与香港黑社会关系的分析文章,准备给沈岳交差。为此,他找了两篇别人的回忆文章,半抄半编了几千字,便把草稿给站长看了看,站长果然称赞不已。他顺口提出要去澳门新光书店收集购买资料,那是一家左派书店,有许多香港买不到的大陆出版物,丁守拙自然满口答应。
其实这是个幌子,他的真实意图是想去趟澳门面见陈明远,了解有关湘江计划的进一步情况,这才是他最上心的。可这两天他用公用电话给澳门站陈明远办公室打了几次电话,却都没人接,为此他心急如焚,既担心陈明远出事,又担心错过获取湘江计划内容而造成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原来他与陈明远约定,除非特别紧急情况,不去陈明远在香港的住处找他。可陈明远一直没有消息,这让他下决心晚上去陈明远家周围碰碰运气。
他打定主意,便安心坐下来整理文章,正抄得带劲,电话铃突然响起。他拿起听筒,传来的正是陈明远的声音。陈明远简短的说了句,“我在香港,晚上老地方吃饭”,便挂了。
田之雄心里又兴奋又忐忑。兴奋是因为陈明远不仅安全,还有可能带来好消息,忐忑则是担心发生重大变故,而他没能及时掌握。
下了班,他跟莫之英说了声晚上去逛书店了,莫之英打小就不爱看书,自然不会跟着他去。
田之雄下了班真的先去了一家书店,在里面逛了许久,顺手又买了本最新版的《新华字典》,确定没人盯着他,这才七弯八拐来到上次与陈明远吃饭的茶餐厅,在餐厅附近留意查看了好一会儿,确定没人跟踪,这才进了茶餐厅,陈明远已经在那个小包间里等候多时了。
一看见陈明远凝重的神情,田之雄预感到他已经知道了一些重大的消息。果然,陈明远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已经了解了所谓湘江计划的大致内容,那就是针对内地代表团出访实施罪恶计划,具体地点是在柬国首都金边,直接负责人是南越第三情报工作站站长廖时亮,具体执行人是高棉组组长张沛芝。
田之雄大吃一惊,直接爆了粗口:“这帮王八蛋,简直是狂妄到极点!”
陈明远点点头:“你要赶紧把情况传回去,让大陆方面做好应对措施。”
田之雄问道:“有没有更详尽的情况,比如具体时间,行动方式?”
陈明远摇了摇头:“他们没提,我也不好问。”
“他们?他们是谁?您的消息渠道可靠吗?”
“绝对可靠!”
“何以见得?”田之雄害怕渠道不可靠造成消息不准确,不仅会误导国内有关保卫部门,更会因判断失误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陈明远狡黠地眨了眨眼:“就是廖时亮和张沛芝两人昨天晚上请我吃饭时亲口说的。”
田之雄又吃了一惊,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两个直接负责人居然把如此绝密的信息告诉陈明远?
陈明远哈哈一笑:“他们俩都是我的学生。廖时亮是1939年入的军统,黔阳班毕业的;张沛芝是越南华侨,也是抗战时就加入的军统,当年抗战胜利时还是他亲手逮捕的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呢。他们从台北回西贡,必定要从香港转机,肯定会来拜见老师,请我吃饭。这些就是他们在席间不经意时说的。他们今天已经回西贡了。”
田之雄恍然大悟。
“另外,沈岳要我们站郭汉提前进行对大陆的骚扰计划,从时间点上判断,看来也是为了策应湘江计划的实施的。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找了些理由,把郭汉他们的计划推迟了。”
陈明远又说:“还有个细节,他们提到是从驻柬使馆内部的人嘴里偶然得到代表团出访金边的消息的,你要内地查一下,到底是谁泄的密;如果有他们的内线就麻烦了,要想办法挖出来。”
田之雄神色严峻站起身:“算了,我不吃饭了,马上回去整理一下,今晚就把情况报过去。另外我在嘉咸街的住处新安了电话,这是号码,有事情及时联系。您多保重!”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陈明远与田之雄握了握手,点点头,目送他匆匆离去。
田之雄回到住处,找出一个白信封。这是邮局最常用的平信信封,印刷量至少以百万计,即便万一落入别人之手,单从信封着手根本无从查找来源。他用热水蒸汽慢慢熏着胶水粘合缝隙,用刀片轻轻揭开,便成了一张平展的白纸。他调好密写水,翻阅着作为密码本的1957版《古文观止》将陈明远透露的计划内容写在信封内页上。趁着晾干的功夫,又找出一张最普通的信纸,刻意隐藏着字迹习惯,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貌似一个偷渡客给乡下亲人的报平安家书。然后将信封按照原来的折痕重新粘好,把信塞进去封好口,在信封上写上广东省某某县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某小队母亲大人收等字样。
他收拾好桌上的东西,把新买的字典和原来的字典一起插在书架上,长舒一口气,站起身,穿上风衣,把信妥帖地放进风衣内兜,顺便望了望窗下的街道。正是这条街最热闹的时候,食客川流不息,叫卖声此起彼伏。陈伯应该在街对面正忙着,他想。
他下了楼,走到陈伯的推车平日里停的地方,却不见陈伯。他在街道找了个来回,也没见到陈伯那辆“陈记鱼蛋粉”的车。
他回到老地方,问了问旁边买钵仔糕的老妇人。老妇人答道,下午就没见他出摊。田之雄有些紧张,追问前几日是否看到陈伯?老妇人回答,前几日倒是见到他。田之雄少许放了心,想着陈伯也许是生病了。
他牢记着陈伯上次给他的地址,便在街上买了些水果,提着找过去。心里盘算着,如果找不到陈伯,就只好启用紧急联络方式---那个邮政信箱了,毕竟情报太过重要而紧急。
陈伯的住处离嘉咸街并不太远,他顺利地找到地址的街道号码,发现是间骑楼下的杂货铺。他问了问杂货铺老板,却发现老板是个哑巴。田之雄用笔在手上写了“陈伯”二字,他才“啊,啊”了几声,指指柜台,又指指自己;又指了指天花板,指了指旁边的窄巷。田之雄大致明白了,应该是陈伯把一楼铺面租给了杂货铺,自己住在二楼,要上二楼得从旁边的巷子穿进去。
田之雄顺着窄窄的小巷走到头,果然看到“陈记鱼蛋粉”的推车和一间小厨房,这大概就是平日陈伯煲汤、做鱼蛋的地方,厨房亮着昏暗的灯泡,里面传来有节奏的沉闷敲击声,间或伴着老人咳嗽和吐痰的声音,空气中飘荡着煲汤的香气。。
他走到厨房门口,看见陈伯披着衣服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用一根木棒用力击打着面前木盆里的鱼肉泥,灶上的大锅里还咕嘟咕嘟熬着汤,雾气蒸腾。他轻轻敲了敲敞开着的厨房门,稍稍提高嗓门:“陈伯。”
陈伯回过头吃惊地说着:“哎呀,是罗先生啊,难为你找到这里来,就今天没出摊,是不是有什么急事?我没耽误事情吧?”边说边站起身来,一脸的焦急和病态显得陈伯十分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