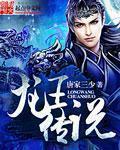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田园生活吧百度贴吧 > 第68章 收玉米(第2页)
第68章 收玉米(第2页)
“是吗?还行吧我没感觉有多好,严老哥你看这一亩地能出多少。”
“这周围就你一家种了春玉米,没有对比你可能看不出来。我这两天刚和朋友从南边完成收割回来,那边种春玉米的多。咱们这边周县市都是收割麦子以后种夏玉米。”
“南边他们一亩地大概在一千两百斤左右,至于你家的这些可能得有一千五百斤。”
姜川惊讶“能有这么多!”
“晒干以后应该差不多。”
“对了严老哥,我看这个收割机的秸秆出料口跟我以前见的不一样,这是新的型号吗?”
严师傅走过去拍了拍车上的铁管子,“你说这个?不新了好几年前就有的型号了。”
“规定秸秆禁止焚烧以后,第一代秸秆还田的收割机出料口就在车尾巴上,口朝下位置很低。”
“后来秸秆直接还田的弊端慢慢显露出来,直接还田不太好,而且原来的那种设计不利于秸秆收集,所以就出现了我开的这种。”
“其实我这个车后面还能牵引一台秸秆打捆机,把两边的料口对好了直接在地里给你把秸秆打包好,很方便。不过我的打捆机出了故障还没修好,也就没带过来。”
“至于现在最新式的是一种,履带式收割打捆脱粒一体机。优点比我们现在用的这种轮式要灵活方便的多。缺点也同样明显新收割的玉米水分含量高,脱粒效果不理想。”
看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才几年一体机都整出来了,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脱粒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姜川猜测大体应该就是装烘干机这类东西,要是做的黑科技一点。以后前面收割鲜玉米后面倒出爆米花的情况都有可能实现。
聊了几句姜川给严师傅结了费用每亩地七十块,黄粱作为朋友去送送,许哲和姜川回去把这最后一车给卸了。
收拾妥当以后姜川去园子里摘了些菜、池塘里捞了条鱼、又买了点肉,让庞伟帮忙打下手,中午把许哲和黄粱留下吃了顿饭。
“黄老哥,这严师傅也是咱们镇上的人吗?”
黄粱往嘴里夹了一片猪耳朵慢悠悠道:“他是镇上西街人,早年听说是出门跑业务跑合同,后来不知道为啥不干了,买了收割机跟人合伙天南海北的下地。我是前几年在县里农机站认识的他。”
“对了,你是怎么想到拿秸秆跟李家村的人换牛粪的?”
姜川摊摊手“我到这来种地种菜的不都得施肥嘛,我又不愿意用化肥所以就换点牛粪呗,村里人应该也有这么干的吧。”
“当然有了,”黄粱放下酒杯开始回忆。
“早年间村里喂牲口的不多,大部分是用来当柴禾烧。后来李家村得了好处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点东西,这样一来饲料就不够用。”
“那时候他们想的办法跟你一样,没钱去买就用些粪肥出去换,所以当时经常能看到李家村的人套着牛车驴车,在四里八乡来回的跑,也就这几年有钱了才买的三轮拖拉机。”
“再后来农资站推广化肥农药,有些村民试了试觉得比用牛粪效果好。于是一部分人就舍弃农家肥改用化肥,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大家对于种子农药化肥产生了分歧。”
“而李家村人觉得,既然你认为我的东西不好那我就不跟你换了,大爷我收钱,从二十、三十、涨到现在的五十。”
“前年的时候县里城关开了个收购站,秸秆一百二十块一吨。每亩地也能多换两百多块。”
说到这里黄粱又干了一杯,面露苦色。“这两百块钱看着不少实际用起来却根本不够。”一旁的许哲知道他要说什么也是心有悲戚。
他掰着手指头给姜川算,“种子要钱、化肥要钱、农药要钱、播种要钱、收割要钱,样样都要钱。”
“但是就靠种粮食种菜能挣几个钱?镇上粮食收购价一块一或者一块二每年都差不多,一亩地也就打个一千来斤。”
“再说咱们农村夏天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点菜,在本地卖不出价,就算想卖到外面去也没有门路。”
“这么一算很明显跟本就剩不下几个钱,怎么办?只能出门打工!”
“村里出去的人多了,平时就没有个村的样子。咱们这里还好,在镇西有个下洼村,村里就剩老头跟娃娃,年轻都跑光了。好在国家心里记挂着农民,免除农业税以后每年还发放补贴,日子多少能好过点。”
坐在一边的庞伟满脸震惊,虽然知道很多人还过着比较贫苦的生活,但没想到能到这个地步。
说到这里黄粱有些似笑非笑的看着姜川,“现在你知道四个村子的人为什么感激你了吧!”
姜川连忙摆手说“不敢”。
“你也不用谦虚,咱们就拿桃花村来说。今年他们村的大白桃零售卖四块,给省城和市里的商场供货也能卖到三块多都不愁销路。要是往年呢?拿到镇上赶集一块五都嫌贵根本卖不出去。这中间差了多大一笔收入!”
“还有咱们村,一开始说要接待游客的时候村里人都觉得不靠谱,最重要的是穷害怕花出去的钱打水漂。”
“最后还是村长以身作则,又花了大力气说服几家做榜样。”接着又看向庞伟,“后面看到你们常来才下定决心,就算是这样有置办不起东西的人家,村长和许家二叔都在经济上帮助过他们。”
“你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