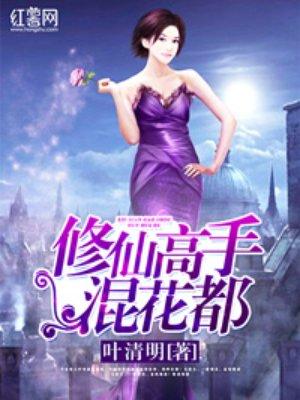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国学大师语录 > 儒学大师谈人生五 学养功夫2(第1页)
儒学大师谈人生五 学养功夫2(第1页)
程颢哲学
程颢与程颐,世称“二程”,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方法。其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先算账,后发火
程颢说: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程颢认为,在人的各种情绪中,最难克制的是怒气。他说:“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怒气很容易发作,又很难制伏,所以最难对付。
怒气一旦发作,对他人的伤害力极大。因为这时候有一泄为快的冲动,凡事易走极端,什么手段最容易伤害对方,就用什么手段,根本不考虑后果。报上曾报道一则新闻,某人跟邻居争论院子里一棵树的归属,一怒之下,竟然将邻居一家四口全杀掉了。他投案自首后,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一棵树能值多少钱,用得着搞出一桩四条人命的血案吗?这样的账,在心平气和时,一是一,二是二,很容易算清。可是等到怒气上来,账就不会算了,可能把一算成一亿,产生原子裂变般的杀力。
“布衣之士”发怒还好一点,“流血五步”而已,如果是权势人物发怒,可能造成“伏尸百万”的结局。
春秋时,齐桓公的夫人蔡姬是蔡穆公的妹妹。有一天,齐桓公与蔡姬乘坐小船在水池中游玩。蔡姬知道齐桓公怕水,故意跟他开玩笑,用手向他身上泼水,还让船左右摇晃。齐桓公惊慌失措。上岸后,他想起刚才的狼狈样,觉得很丢面子,认为蔡姬的玩笑开得太过分了,一怒之下,将她送回了娘家。
蔡穆公见妹妹被送回来,觉得很没面子,一气之下,就自作主张,把蔡姬改嫁给了楚成王。
过了一段时间,齐桓公的气消了,派人去接蔡姬回来,谁知她已经改嫁了。齐桓公大怒,就想出兵蔡国。可是,为了一个女人打仗,名不正言不顺,国内老百姓不乐意,传出去也怕被诸侯笑话。于是,他利用霸主身份,以楚成王不向周天子进贡为名,联合诸侯,出兵降服了楚国,顺便把蔡国灭掉了。
你瞧,一个人发怒,使十几个国家卷入战火,牺牲了无数条生命,灭亡了一个国家,破坏力大不大?最冤枉的是楚国,又没招惹人家,无缘无故被人揍趴了。就像俗话说的:混龙闹海,鱼虾遭殃。
怒气一旦发作,不仅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有时候,自己所受的伤害可能更大。
春秋时,楚国卑梁与吴国交界。两国边民相互往来通婚,关系很友好。有一天,一群姑娘们在一起劳作、娱乐,一位吴国姑娘不小心弄伤了一位卑梁姑娘。这本是小事,卑梁姑娘的父亲却不服气,带着女儿去吴国姑娘家里评理。吴国姑娘的父亲非但不道歉,态度还很不友善。卑梁人一怒之下,将他杀了。
当地的吴国人闻讯后,群情激愤,你呼我唤,邀集了一大群人,越过边境,将卑梁姑娘一家人都杀掉了。
卑梁的地方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大怒,亲自率领兵马,将这个村子里的吴国人杀得鸡犬不留。
吴王得到报告后,十分震怒,马上派大军进攻卑梁,并把它夷为平地。
自此,吴楚两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互有胜负。最后,吴国的公子光率领大军在鸡父与楚军主力决战,大获全胜,乘胜攻占楚国的郢都,俘获了楚平王的夫人,把她带回了吴国。这场战争总算告一段落。日后双方还进行过多起战争,当年埋下的仇恨很可能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居然导致多人死亡、两国成仇、国母受辱,这笔账怎么算都花不来。可是,当初怒气发作的时候,谁会去算这笔账呢?
假如一个人能克制自己的怒气,就很少做后悔之事了。正如程颢所说:“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意思大致是说:只要能在愤怒的时候,能够让怒火顿然熄灭,而审度道理的对错,就会发现,诱发怒火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讨厌,没有那么可恶。这时候,差不多也能做出正确反应了。
问题是,愤怒的时候,怎样才能“遽忘其怒”呢?要先算账再发火,不要先发火再算账。先把火气发出来了,到最后才来算账,往往越算越后悔。不如在火气发出来之前,先把账算一算:如果我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呢?会有什么坏处呢?如果我不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呢?会有什么坏处呢?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会有什么好处呢?会有什么坏处呢?这样算账,不一定能算得一清二楚。但你能想到要算算账,头脑已经冷静下来了,就不会做那种后悔莫及的事了。
“书不必多看”
程颐说:书不必多看,要知其约。多看而不知其约,书肆耳。
“书不必多看”,这句话说出来,能吓人一跳。从小到大,老师、家长就告诫我们:要多读书!要多读书!越多越好。程颐老先生却说反话,认为书不必多看。那些对学习兴趣不大的学生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欢呼雀跃,遗憾程颐老先生不是自己的老师。
可是,程颐说这句话,有一个前提:“要知其约。”一定要掌握要点。这就比较困难了。比读书本身还困难。一部《论语》,二万余字,读得快的,一小时就够了,读得慢的,二三小时也能读完。可是要掌握它的全部要点,花半辈子功夫恐怕还不够。如果是读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读起来又快又轻松,更觉容易。可是要看出其中得失要点、写作技巧、遣词方法之类,就不那么简单了。
不要说掌握一本书的全部要点,每读一本书,能够总结出一句话、一个词,就很不简单。鲁迅到底读了多少书,我们不知道。他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看书时看见满篇都是“吃人”二字。这两个字就足见鲁迅先生不简单,抓住了中国专制文化要点。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归根结底是一种人吃人的制度,一切的学问,无非是研究如何吃得多、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文明。千古以来,读书的人那么多,读不出“吃人”二字,鲁迅先生能读出来,他就比别人高明。
不要说总结自己的观点,每读一本书,能够记住其中一句好话、一个好词,就算没有白读。可惜这么简单的事,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一本书读完,就抛诸脑后,大不了能记住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其余的什么也没有留下。像这样读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如程颐云:“多看而不知其约,书肆耳。”书读得多却不知道要点,不过像开“书店”罢了。
程颐为什么不说“书房”而说“书店”呢?因为书房里的书,通常会永久保存;书店里书,随进随出,都是暂时存在。如果读书像布置书房一样,虽“不知其约”,起码可当“知识广博”四字,也不简单了。多数人读书像开书店,随读随忘,留下的说不定还是不好卖的。比如鲁迅笔下那个孔乙己,书读得不少,连自己都养不活,买书的钱都挣不来。他读书的最大用途,不过是跟小孩子卖弄“多乎哉,不多也”和狡辩“偷书不为贼”罢了。
如果读书“知其约”,真的没有必要多读书。《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成绩太差而被劝退学。老师对他的评价是:“既没有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可是他却成了大文豪。这说明他虽然读书不够多,却掌握了成为文豪的要点。
中国也有很多读书不多却能成就大器的人。比如宋朝宰相赵普,相传他“半部《论语》平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一说法并非野史所传,而是出于正史。据《宋史》说,开国丞相赵普每遇政事不能决,便于归家后查阅家中一箧中书,次日问题便迎刃而解。久之家人好奇,偷偷发箧一看,原来里面只有半部《论语》。于是时人便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宋朝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也记载说:“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