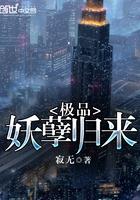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清风不识君是什么意思 > 第100章 皇子之争(第1页)
第100章 皇子之争(第1页)
匈奴来势汹汹,已然兵临城下,开始疯狂攻城。
朝堂之上,每日里那奏折似漫天飞雪般纷至沓来,直让皇上烦闷不已。
虽说此前已将监国重任托付给太子,可毕竟皇上龙体尚安,诸多关乎国运的大事,终究还得仰仗皇上圣裁,故而文武百官皆是心急如焚,吵嚷着定要面见圣上。
皇上无奈,只得应允,于乾清殿中召见众人。
太师上前,神色凝重且言辞恳切,朝着皇上深深一揖,朗声道:“陛下,如今匈奴肆虐,云中危在旦夕,还望陛下尽快钦定此次出征的主将人选,即刻点兵驰援云中,以迎强敌啊,若再耽搁,云中百姓恐将惨遭涂炭。”
皇上听闻,无奈地一摊双手,满面愁容道:“众卿皆言打仗,可这打仗所需的银子又从何处来?朕自登基以来,这几年间,北方久旱不雨,赤地千里,南方又逢洪灾肆虐,百姓苦不堪言,好容易熬过这两灾,如今却又闹起了虫灾。
年年皆因灾荒而减免赋税,各个县能上缴多少税银?户部如今又能否拿出三百万两银子来?没了银子,拿什么去支撑这战事啊?”
秦太师眼珠一转,赶忙上前一步,拱手奏道:“陛下,这仗自然是不能不打的,可这银子,却也能设法筹集。
此事依臣之见,不如交予三皇子去操办,且让三皇子随军出征,讨伐匈奴。
臣斗胆推举臣家中长子秦审言担此主将之任,他身为兵部尚书,身负报国之责,如今正值国家用人之际,理当为国为民效犬马之劳,恳请陛下恩准。”
敬国公见状,也毫不迟疑,疾步上前,拜倒在地,高声道:“陛下,此事交由太子殿下才是正理。
太子殿下亲率大军出征,方能大振我军士气,扬我大国之威。
臣那犬子,现为忠武将军,曾多次参与高丽、鲜卑之战,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还望陛下准许犬子担任主将,前往云中御敌,臣担保犬子定当拼尽全力,不击退敌军,誓不还朝。”
秦太师狭长眼眸微眯,眸中隐有精光,继而昂首,声若洪钟道:“太子殿下监国,身负家国重责,身份尊贵至极,实不宜涉险亲赴那刀兵之地。
三皇子,乃太子手足至亲,血脉相连,于公于私,皆有责分忧于圣驾,效力于兄长。
且三皇子亦是圣上亲子,身位尊崇,若由其率军前往,必可大振士气,此为上佳之选。
敬国公,莫再多言了。
那薛将军既为忠武将军,自当以护卫宫城安危为要,今太子监国,有薛将军守护皇城,方可使圣上无后顾之忧,此乃最为妥善安排。。。。。。。”
敬国公哪容秦太师尽言,未待其话音落定,便面沉如水,厉声驳道:“太师此言差矣!
圣上龙体安康,圣明远播,委太子监国,本就是对太子之磨砺,期其日后可担江山之重任。
值此用人之际,太子殿下身为圣上长子,诸皇子之长兄,自当身先士卒,垂范于众,为圣上分忧,解百姓倒悬之危。
由太子殿下亲赴前线,方为名正言顺之举。
若三皇子果有赤诚之心,欲尽忠尽孝于皇上,那便令其筹措军资,安置粮草,以使前方将士安心征战,无后顾之忧,此乃正途也。”
众大臣闻此,心中暗忖,皆觉这敬国公着实老谋深算。
那筹集银两之事,本就是难如登天,敬国公此举,分明是让三皇子费力筹措,却只为太子做嫁衣裳。
太子只要往军中一行,军功、美名皆可轻易收入囊中,可三皇子即便费尽心力凑齐银子,亦是分内之事,无人会赞,稍有差池,便会落得个不忠不孝、未尽全力之名,真真是将三皇子置于炭火之上,使其进退两难。
秦太师岂会不明敬国公那潜藏之意,分明是欲使三皇子为太子铺就功勋之路,只是太子能否稳稳接住,尚在两可之间。
太师略作思忖,遂拱手向皇上揖礼,恭声道:“皇上,既如此,莫若令三皇子与太子殿下自行定夺,且看哪位皇子愿往那险地一行,也好彰其忠君报国之忱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