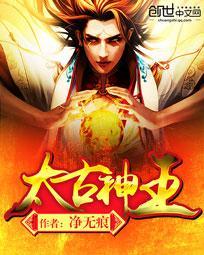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南宋动荡吗 > 0172章 长歌当哭(第2页)
0172章 长歌当哭(第2页)
李伯言拔开瓶塞,遥望岳麓,心中暗道:晦翁啊,晦翁,某在等你迟来的认输,这千百民夫,同样再等你的祝福,您可曾听到了?
可曾看到海晏河清的未来盛景?
可曾看到,那盛世之下,一派歌舞升平的真太平?
……
……
岳麓书院之中,所有人都心绪不宁。
这本该是一个家中团聚的日子,有的湘潭学子离家近,已经回去,而有的人呢,则是不远万里,追随晦翁来到此地。
一声声水调歌头,唱得他们泪眼朦胧。
后院厢房之中,黄幹、陈淳等人,面如死灰。
攻心之计,呜呼哀哉!
涌上的三位先生,已然回了明州四明老家,准备隐居于山中。眼下岳麓书院,分崩离析,没有任何的挑拨离间,只因为大势所趋,人心涣散。
那套治国安民的大道,再也难以说服他们自己,能够静下心来,去面对天灾,面对永嘉新学。
黎贵臣走入杉庵,见到晦翁依旧在注疏着《易书》。
听到有人进来,朱元晦不由自主地说道:“季通啊,季通,你来说说,这句……”
“先生,是我。”
朱元晦放下笔,笑道:“哦,昭文啊,唉,糊涂了。季通一月前回道州了啊,真是,年纪大了。”
“先生这是有什么要帮忙的?”
朱元晦摇手,笑道:“你帮不上。要是季通在,这《易书》最后一章句,还能与我交流探讨,你啊,不愿读这著说,所以啊,不可与你谈《易书》。”
黎贵臣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拱手道:“是啊,西山先生起稿的《易学启蒙》,真是发人肺腑,建阳蔡氏九儒,学生不及也。”
“人读易书难,季通读难书易,好啊……好啊。昭文,你过来所谓何事?”
黎贵臣一滞,耳畔歌声依旧,他立马关了门。
“关门做甚?”
黎贵臣神情有些不自然地说道:“外头太嘈杂,怕打扰先生著说。”
朱元晦笑道:“伯言的中秋诗会,真是别开生面啊。”
“先生你……”
“呵呵,没关系。这是伯言再向老朽讨一句话呢。”
黎贵臣一愣,问道:“什么话?”
朱元晦哈哈一笑,没有明说,而是说道:“昭文,天色晚了,回去睡吧。明日起来,记得将杉庵之中的落叶清扫一下。”
“哦……那学生告退了。”
黎贵臣退出房门,见到黄幹、陈淳还有辅广,都面色不佳地看着他,便道:“老师没什么,就是累了,要睡了。”
辅广靠近,低声问道:“老师没有说,这个传唱的水调歌头吗?”
“倒是提了一嘴,笑着说的,还说是欠李家小子一个答复。”
黄幹插嘴道:“答复?什么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