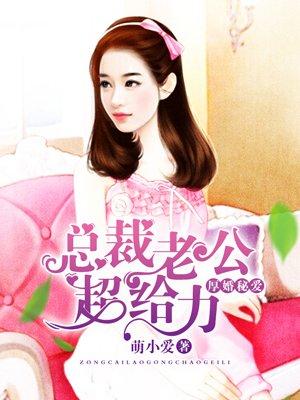去看看小说网>走出至暗时刻的能力更重要 > 第二十一章 描摹匪事(第2页)
第二十一章 描摹匪事(第2页)
两个匪徒倒在了血泊中,匪首的胳膊上也挨了一枪。匪徒们都傻了眼,慌忙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匪首捂着伤臂痛歪了脸,恼恨地大声叫骂:“二赖,我×你先人!你敢欺哄老子!那枪子是从你妈×里钻进来的!”
此时老汉才幡然醒悟,是外甥给土匪做眼线来抢劫他。怪不得那崽娃子舍得带一斤点心来看望他,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来拜年。老汉气得浑身筛糠,差点儿背过气去。
再后来,二赖不敢再见这家匪首,去投另一个山头,没料到那个山头的匪首竟然不收他,骂他猪狗不如,对自己的亲娘舅都能下黑手。二赖连当土匪的资格都没有。
原来,盗亦有道。
说者无意,可听者有心。听的故事多了,我就滋生了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的念头,可迟迟没有动笔。恰在这时,邻村一位老者来家给我讲了一段他表叔家的往事。他表叔是个车把式,家道十分殷实,走南闯北,交际很广,特别是与一个土匪头子交往甚密。一次,那个土匪头子出山作案,返回时在他表叔家歇脚过夜,见他表叔独居的嫂子貌美如花,竟然摸黑进屋把他表叔的嫂子奸污了。他表叔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在肚里直骂土匪头子是个畜生,却也知道土匪头子心狠手辣,而且手下个个都是亡命之徒,只能忍下这口恶气。后来为报此深仇大恨,他表叔去投了军。在部队上,他表叔作战勇敢,很受团长的赏识。团长也是陕西乡党,提拔他表叔做了卫队队长。再后来,他表叔把自己的深仇大恨说给了团长,团长便让他表叔带着卫队回去收拾了那个土匪头子。故事曲折离奇,充满传奇色彩。
这个真实的复仇故事一下子激活了蛰伏在我心底的创作欲望。可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从没见过土匪,仅仅靠听来的故事去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肯定是不行了。我便向书本求教,找来许多研究土匪的书来读;又找来武功、扶风、周至、乾县等县的县志仔细翻阅,了解滋生土匪的原因及时代背景,探寻土匪的历史渊源,为创作做前期准备工作。
什么是土匪?《辞海》对“土匪”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以聚众抢劫为生,残害人民,或者窝藏盗匪,坐地分赃的分子。”追溯历史渊源,关于土匪人物的最早记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中。土匪在中华大地存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土匪活动以特有的方式在中国广袤大地普遍存在,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不容偏废的一个侧面。在陕西关中潼关以西、宝鸡以东的渭河两岸以及渭北高原,经常出没着一帮镖客,他们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刀子,人们把这些镖客称为“关中刀客”。关中不出剑客,剑客文弱了些。关中汉子的脾气秉性是生、冷、蹭、倔。他们自嘲为“关中愣娃”。关中愣娃爱耍刀,所以关中出刀客。刀客们在刀尖上讨生活,他们带的刀长约三尺,宽约两寸,用好钢铁打造而成。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保私盐、保私茶,也保大户人家的千金、漂亮媳妇和金银珠宝,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遇到催粮要款的,他们眼睛向天,露着胸脯,敢跟当兵的玩命。到了火器时代,刀客与时俱进,不仅耍刀,更多的时候是玩枪。
刀客在官府的眼里也是土匪,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永远是被缉捕的对象。
翻阅大量史料,我对刀客、土匪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知。刀客、土匪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其种种暴行尽管有着人性深处“恶”的种子的萌发,但更根本、更重要的还是社会的极端不公和为富不仁行为,促使、导致、逼迫普通的民众为生存、为活命、为公道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可以说,是恶劣的社会环境导致中国土匪、刀客问题的不断出现。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关中人,我从小对关中的认知就是宝鸡、西安、咸阳三市,更官方的解释是“四关”(即潼关、散关、武关、萧关)之内,城市还需再加上渭南、铜川。关中是陕西地理位置、环境条件最优越的地方,历朝历代都是经济繁荣的地区。可在1929年,陕西关中地区发生了特大灾荒,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有道是:“饭饱生娱事,饥寒生盗贼。”饥馑令民不聊生,也为陕西刀客、土匪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加之军阀混战,这一社会背景使陕西省会西安一度成为各色武装团伙的聚集、争战之地,更是对陕西刀客、土匪的蔓延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民国时期的陕西可以用“无时无匪、无处无匪”来形容,当时关中地区经济衰败,“当兵领饷”和“当匪行劫”成了很多穷人的选择。正是由于此,在关中渭北一带几乎每个村子都流传着刀客、土匪的传奇故事,甚至有些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连年饥荒、饿殍遍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景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与此同时,墩子、刘十三、马天福、马天寿、秦双喜、彭大锤、贺云鹏、喜凤、碧秀、许云卿、罗蛮蛮等人物形象也在我胸中日渐凸显出来。
我觉得可以动笔了。可如何去写?如何让人物活起来?如何才能把这段历史比较真实地描摹表现出来?我又陷入了深思。我太想写出一部厚重有分量的作品来。在我心目中,好作品一定要好读,要有故事,故事是小说的核心,但故事不是小说的意义,小说应该提供心灵与生活的状态,提供可能性与想象性,表达普遍性的日常与日常普遍的个性;而且,文字必须通畅,我不相信有谁愿意读佶屈聱牙的文章。
要把小说写得更像小说,这是我动笔涂鸦一直的追求。小说要写得能让读者读得下去,而不是读不下去。小说要让读者在阅读中享受到文字的美好,抑或在故事情节中感受到快乐,在快乐中欢笑并击节叫好;抑或悲愤流泪、黯然伤神,乃至进行深思。如果把小说写得如同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谁还会去读?
我有许多朋友,他们大多不是作家,但他们喜欢读书,爱好文学,我常与他们闲聊文学。他们说谁谁谁是大作家,可其作品自己就是读不下去,也不知道其代表作是哪本书。
于是我就想,写小说其实也就是讲故事,只有把故事讲好,作者斐然的文采才有所依托,深邃的思想才能被读者接受。倘若你的作品没人喜欢看,你的文采你的思想谁又能知道?
再者,我以为写小说就是作者与读者聊天,用陕西话说就是“谝闲传”,不是与陌生人谝,而是和朋友谝。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魔幻玄虚、志异怪味……啥都可以谝,但不可用教训人的口气,不要扮演教主的角色,谝者高兴,听者愉悦,如此而已。如果作者自己的信仰、思想、学养在聊天中能被读者欣赏,甚至愉快地接受,那他就是高手。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据说现在有种说法,作家只想着把故事讲好是没出息的表现。若是如此,我这辈子注定是个没出息的人。
土匪的故事几乎都带有传奇色彩,跌宕曲折,甚至荒诞离奇,把这些写出来一定会有读者的,我充满着自信。可这样的作品能不能出版,我却很不自信。我无意为土匪树碑立传,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
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那就写吧,写出来再说吧。
二
我开始动笔了,时在1994年年底。
小说写得很顺利,心中的人物在我的笔下跃然纸上,我随着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而情绪起伏。不该死的人要死了,我的心很沉痛,甚至落泪;该死的人却活着,我很是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有时心静下来,我会为自己感到可笑。人常说看戏流泪,替古人担忧;我这是写书流泪,替书里人伤心。
后来许多读过我“关中匪事”作品的朋友都说我写的土匪很有人性,甚至很善良,不让人痛恨。我在翻阅大量史料时发现,许多土匪,甚至书中记载的很残暴的匪首并不是天生就是坏人。譬如一个杀人如麻的匪首却十分孝敬他的老娘,老娘的话对他来说犹如圣旨。他老娘吃斋念佛,他只要是陪着老娘吃饭,决不动荤,甚至滴酒不沾。还有一个匪首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后来闯荡江湖当了山大王,但凡遇到乞丐他都要给予施舍。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下,与人为善已成为国人做人的基本准则。善良本分、安贫乐道的中国农民是不会轻易走上犯上作乱的道路的。他们深知做盗匪是极不光彩的,不仅会遗臭万年,而且会累及后辈儿孙。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们宁可去死,也不愿走上违法之路去抢劫掠财。
土匪谈不上有政治性的阶级觉悟,但朴素的阶级感情还是有的。这种感情促使有的匪伙始终把行动目标对准财主富绅。显然,这样的匪伙头领的正义感和对地方的责任意识比较强烈。他们虽为匪人,但人的良知和古朴的人道精神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情绪或行为。关于盗跖对“盗亦有道”的诠释他们不见得通晓,但对“盗亦有道”的本身含义,他们是明白并有所体会的。于是,出现一些行事“仁义”的土匪就不足为奇,也给污名秽行的土匪行为带来些许亮色。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匪患泛滥于社会失序、国家分裂、遍地烽火狼烟的乱世,净化于国家统一、强盛的社会环境里。匪患兴起作乱于乱世,平息于盛世,这是历史的结论,毋庸置疑。
写到大约一半时,一天,我摇着轮椅去西农大校园闲游解闷。首次写长篇,烧脑劳神又费力。那时没有电脑,用手写,写完一章,手指头僵硬得都伸不直,得放松放松。也是巧,路上邂逅一位文友。闲聊时,他问我在写什么,手中有没有长篇稿子,他有一位在西安的姓王的朋友在做一套“黄土地文化丛书”,需要长篇稿子,我便说了正在写的长篇。他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他在西安的朋友。一星期后,我收到了王某人的约稿信,信中言辞十分恳切,让我尽快把书稿完成,他帮我出版。有人约稿,自然是大好事,我便夜以继日赶写书稿。其间,我心存疑虑,因为写的是匪事题材,我怕不好把握,便写了封信给王,并讲了小说的故事梗概。王对书稿十分感兴趣,三天里我接连收到他的两封来信,信中言辞由急切变为迫不及待,让我赶紧把稿子赶出来,他不日派人来取。未等我复信,取稿的人来了,是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还带着王的一封亲笔信。是时,书稿只写了一多半,还未誊清。给还是不给,我很是犹豫。来人说,王说了,不必另誊,把毛稿带去就行,王用电脑帮我打。我还是犹豫不决。来人又说,王和他都是扶风人,他们都是乡党,还有啥不放心的。我这才把写好的稿子交给来人。
不几天,王又来信催稿。一月后,我完成了全部书稿,托人带给王。
几天后,我收到王的信,信中他对书稿大加赞赏,说是有朋友看上了书稿,愿帮忙向出版社推荐,让我写一份二百字简历,并附上一张彩照、一张黑白照以及身份证复印件和两份委托书一并寄予他。我一一照办。
此后,我耐心地等待佳音传来,但迟迟不见任何消息。实在等不及了,我去信询问,却没有回音。就在我焦急不安之时,王突然来到我家,和他同来的有他的一位朋友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印刷厂的段厂长。
这是我和王第一次见面。王给我的印象很不错,他年长我十多岁,戴一副眼镜,颇有学者风度,说话嗓音洪亮,谈吐虽粗俗却不失风趣幽默,像是性情中人。闲谈中我得知他是扶风绛帐人,曾在陕北某县任文化馆馆长,现在在做图书出版方面的工作。绛帐距我家乡仅二十里地,不用套近乎,我们也是乡党。对这样一个人,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王告诉我,他在做一套“黄土地文化丛书”,都是长篇小说,我的书稿他仔细阅读了,可以肯定地说,是这套丛书的领衔之作,而且有朋友很看好此书稿,愿帮忙出版,但嫌单薄了些,还提出了修改意见,让多增加些有可读性的东西。临走时他再三说,一定要按他的意见修改。
我便下功夫修改书稿,但没有完全按王的意思去改。我实在写不出他建议的故事和情节。书稿改好后,我托人给王带去,期盼着好消息。
1996年2月,我收到了王的来信,告诉我书稿已交给朋友,让我放心。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此后却再没有消息。王让我放心,可我怎能放心得下?书稿就是我的“孩子”,把“孩子”交给别人,谁能放心得下?焦急之中我多次写信给王,询问情况。王没有回信,只是让人带口信给我,说书稿一直在洽谈中,让我耐心等待。我别无他法,只好耐心等待。
然而,还是一直没有消息。我失去了耐心,频频去信询问(那时家里没有装电话,即使装电话,也不知向何处打),并托朋友去问,却不见回音。
在我不断的催问下,1997年5月上旬,王回老家探亲,顺便来到我家,告诉我书稿出版要等到明年。我说,既然如此,那就算了,把书稿还我吧。王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书稿仍在洽谈中,让我不要太心急。尽管我对他的人格已经产生了怀疑,可天生面软,不好再说啥,只好再相信他一次。
王此次走后,如泥牛入海。我感到情况不妙,多次托朋友向王索要书稿,王每次都以“书稿仍在洽谈中”回绝我。我拿他实在没办法,搞得都没了脾气。